

梨树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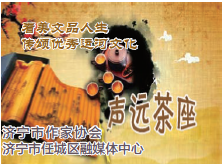

李冰
1944年冬日的胶东,凛冽的北风呼啸着掠过河头店镇李家泊子村。铅灰色的天空低垂,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寂静中,连往日的炊烟都消失无踪。村边的小河静静流淌,清澈的河水蜿蜒环绕着这个萧索的村落,最终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。山丘上几株老梨树在寒风中瑟缩着枝干,默默俯瞰着这片荒凉的丘陵。
麦田里,一位身材敦实的老农弓着背,在一棵梨树下机械地铲着杂草。他眉头紧锁,手上的动作时快时慢。“三儿今天就要离家参军了,孩子还那么小……”老人不敢面对离别的时刻,只能借劳作来逃避。铁铲起落间,有的杂草被连根铲除,有的则因老人心不在焉而侥幸存活。
远处,一个瘦削的身影正快步奔来。少年黝黑的脸上还带着稚气,肥大的棉袄用皮带草草束着,单薄的夹裤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刺目。他气喘吁吁地跑到父亲身边,二话不说夺过铁铲就开始卖力地铲草。
“爹,我走了,您别惦记,我能照顾好自己。”少年低着头,声音闷在棉袄领子里。
老人怔怔地望着儿子麻利的动作,半晌才轻轻叹了口气,用粗糙的手掌抹了把脸,慢慢从儿子手中拿回铁铲。“三儿,你娘……还好吧?”他停下动作,望着这个才到自己肩膀高的儿子。忽然像是被风沙迷了眼,老人抬起右臂,用破旧的袄袖擦了擦眼角。
少年始终低着头,声音有些发颤:“俺娘在家里哭呢……”他顿了顿,强压下哽咽,“俺就不回去了,跟爹道个别就走。老师和同学们都在下泊子等着,今晚必须赶到区里,咱们的队伍就在那儿。”
老人打量着儿子空荡荡的双手:“三儿,你娘熬了一宿给你赶了条棉裤,还纳了双新鞋……”
“老师说部队上啥都有。”少年下意识按了按鼓鼓的棉袄口袋,抬头望向身旁的老梨树。这棵见证他长大的老树静默伫立,斑驳的树皮在寒风中微微颤动,仿佛在用无声的目光送别这个它看着长大的孩子。
他随手折下一根细枝,在空气中划出几道弧线。目光越过南边连绵的丘陵,想到即将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奔赴战场,少年的胸膛里顿时涌起一股热流。
“爹,鬼子天天杀人放火,不把他们赶走,咱们就得永远躲下去。”少年挺直了腰板,手中的枝条猛然向前一挥,在冬日苍白的阳光下划出一道凌厉的轨迹,“老师说,只有打跑这些畜生,咱们才能真正当家作主!”
老人清楚地知道,十五公里外的莱阳县城就驻扎着日本鬼子。那些恶魔的飞机时常在村子上空盘旋,下乡扫荡的队伍像蝗虫般抢掠烧杀。整个李家泊子村的百姓都活在恐惧中,不得不一次次“逃反”避难。儿子在高庄沟村当代课教师这大半年,跟着咸盛斋老师学文化、练枪法——那支“马拐子”短步枪都快赶上他个头高了。如今咸盛斋老师被人告发了,共产党员身份已暴露,需要转移,这孩子也要跟着去参军。这是光荣的事,可他才十四岁啊……
老人颤抖着手撩开棉袄大襟,摸出张皱巴巴的北海银行五元票子:“三儿,常来信。”纸币上“抗日救国”四个红字格外刺眼。
少年接过带着父亲体温的钞票,喉头滚动:“爹,二哥在下泊子等着呢,俺走了!”他用力拍了拍老梨树龟裂的树皮,头也不回地迈开步子。
“希绪!”父亲突然喊出这个久违的名字。少年浑身一震,上次听父亲这样叫他,还是送他去塔子寨读书那年。他举起手挥了挥,不敢回头,眼睛里蓄满了泪,生怕一转身就会溃堤。
“知道爹的大名吗?”苍老的声音追上来。
少年停住脚步,转身看见父亲佝偻着靠在梨树上:“不是叫李子厚吗?”
“那是号。”老人折了根树枝,在冻土上一笔一划地写着:“俺叫李守堃,和你太和荣大伯的‘坤’字不一样……”黄土地上渐渐显出两个端正的汉字。
少年突然泪如雨下:“爹,俺记住了!”他知道此去枪林弹雨,归期渺茫。
老人倚着老梨树,看着儿子瘦小的身影消失在山路上。远处连绵的梨树林在寒风中摇曳,就像这些年一个个走出村子再没回来的后生……

